凯松的昨天与今天
凯松村民主改革采访日记
林田
(林田,新华社高级记者,1950年随十八军进藏,先后任新华社驻藏记者6年,写了大量有关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的报道。)
1959年6月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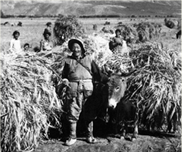 |
| 民主改革后第一个收获的季节,凯松乡农民次仁欧珠赶着自家的毛驴驮运青稞。 |
太阳升高时,我们来到一个水渠纵横、庄稼茂盛的去处,远见一个紫色围檐方城堡似的大房子,从一片树林中露出一角。这就是凯松谿卡了。据说这是西藏叛乱集团头子索康·旺清格来的祖辈--老索康家起家的庄园。民主改革试点工作组来这里工作了一些日子。我们的车子一到村头,光屁股的孩子们就跑过来招手。汽车刚停下,村民们就来帮我们搬行李,领我们进了大庄宅。这是一座古老的石砌的“口”字型的三层楼建筑,典型的庄园主住宅。走进大门,从左右两侧可以进入天井,天井四周楼底是马棚和仓库。大门正对面几步远是一个双走道大楼梯,楼梯板被奴隶们的赤脚磨出了一个个窝窝。楼上二、三层正厅是主人的居室和经堂,窗外垂着宽大的黑色牛毛帘幕,两侧和正厅对面,是其他人的住房和灶房等。我们被安置在三层楼上,空洞洞的大屋子里一股灰尘气味,外檐下麻雀、燕子噪个不休,整个宅子给人一种荒废的阴森森的感觉。
二楼灶房里,一个老婆婆看着灶火,她灰发蓬乱,目光呆滞。听说她十二三岁就到庄宅里当朗生,已50多岁了。一楼马槽围了大房子一周,足可拴成百匹马,但马全被参加叛乱的主人带走了。门口还有一个独木舟样的大马槽,槽下躺着个老马夫。听说他是给庄园养了40年马的朗生。他一生冬天住马棚,夏天睡草房顶,这次工作组来了,才给了他一间屋子,但他有时还习惯地躺在大马槽下。这老人满脸的皱纹使眼睛鼻子变了形。
下午,工作组召开全庄园农奴大会,选举农会筹委会委员。
 |
| 民主改革前山南凯松庄园的朗生用手工纺线为农奴主芝差。 |
大会开始了。人们仰着头,半张着口。听着从没听过的话。工作组的张同志说:“诸位老乡们!今天是我们这些受苦的人,受压迫的人,自己人,开第一次大会。开会做什么?大家知道,你们的主人索康叛乱了,跑了,‘谿卡堆’(庄园主代理人、管家)也跑了。压迫你们的人垮台了。我们要选出自己的人来领导大家,领导我们翻身,过新生活。……谁来领导呢?不识字的人行吗?女人行吗/都行啊!只要心好,办事公正,大家信得过就行……”
人们嘿嘿笑了。“我们要成立一个受压迫的人的组织,种庄稼的人的组织,农民协会,今天先成立农会的筹备委员会。”这两天,人们已经提前进行了酝酿、选择、比较,现在候选人名单公布了。“主任委员尼玛次仁!”大家望一望人群一角的一个青年人。他面色黝黑,额头突出,深眼窝里闪出深沉又带点憨气的目光。这个小个子青年从9岁起就接替去世的父亲到凯松谿卡当“差徭”(一种作农活的奴隶),已当了15年。人们听到他的名字,有的咕噜道:“他从小受苦,不会向坏道上领我们的!”姑娘们笑一笑。“副主任委员基嘉!”人们又用目光找到了那个高个儿大脸庞的姑娘。她害羞了,低下了头,两只大手摸着破裙子。她是个朗生,讲起身世,她说过:“我不是吃糌粑长大的,是受苦受罪、挨打挨骂长大的!”她的主人,给她吃一个人四分之三的口粮,要她干两个半人的活。人们对她当然是信得过的。还提出了一个副主任委员乌金,一个面孔黄黄的差巴。还有委员阿旺、多吉等,包括正副主任共9个委员,其中4个是朗生和差徭,3个堆穷(意为“小户”,是一种没有“差地”,向领主交纳人头税并服一定劳役,靠租种小块土地、作小手工业或打短工为生的农奴),两个差巴。
人群分成了三堆,开始讨论,在堆穷这一堆里,一个络腮胡子、脸上的皱纹成了小壕沟的老人从草地上站了起来,一看就知道,这老人虽然在饥寒中度过了将近一生,但仍有顽强的生命力,他名叫拉珠,说道:“诸位邻居亲戚们!今天是我们祖祖辈辈第一次自由地做人,头一遭由我们自己挑选人,挑选出来,不是压迫我们,不是打我们、骂我们,而是领着我们翻身。……尼玛次仁年轻,基嘉是妇女,可是他们都是咱自己人,我们从他们会走路时就看着他们受苦,他们是不会领我们走歪路,不会忘掉我们的。我们要翻身,要自由,过好日子,就要选这样的人。我们都是从昏睡中刚醒过来,需要共产党和我们挑选的人用手牵着我们走路……”
朗生一群里,大家只嘿嘿笑,没人讲话。他们当奴隶受压迫太重了,一时还不习惯于独立发表意见。沉默了好久,笑了好久,一个老妈妈低声说了:“今天这位本波(长官)说的,是我们心里的话,大家挑选的,是我为他们祷告的人。”
“可是我不会说什么,我不会说什么!”说着,她把两只粗节而枯瘦的手合在一起,拜着,颤抖着,没有牙齿的嘴也在哆嗦着:“吐吉其啦!吐吉其啦!”(谢谢啦!谢谢啦!)
差巴一群里很活跃,他们过去虽然人身也依附于领主,但和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朗生不同,见识也多一些,所以对候选人一个个议论了一番。
最后,人们在阳光照耀的林中草地上坐了一圈。尼玛次仁、基嘉、乌金、多吉、阿旺等站在圈中桌子前面,他们额上、鼻子上出了汗,眼睛放出喜悦的光采。围着他们的人把手高高举了起来,这是一些终年劳碌的手,被人支配的手,今天第一次自由地举起来,在这个庄园前面,过了第一次民主生活。
1959年6月7日
中午,在大门外水池边遇到了其美错姆老妈妈,她家是四代朗生了。晚上我们访问了她。老妈妈白发蓬乱,满脸皱折,穿一件牛毛羊毛混织的粗褐衫子,这是她唯一的一件衣服,夜里又当被子。她两只脚黑黑的长着厚皮。谈话时头老在打颤。许多事情,她已记不清了。只记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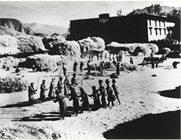 |
| 民主改革前凯松卡的农奴在打场。 |
她的母亲就给索康凯松谿卡当朗生。父亲是一个差巴户的朗生,常年代替这差巴到谿卡来支乌拉(服劳役)。有一年冬天下大雪,父亲被派到浪卡子出乌拉,一去没回来,后来听说是死在那里了。不久,母亲瞎了,聂巴(管家)想起来就给点吃的,想不起来就不给。不多日子,就连饿带糟踏死了。那时她才8岁,老妈妈用手比划:只这么高!她的手离地3寸,表示很小很小。虽然谿卡有许多空房子,但朗生们从来不准进房子里住,他们只能睡在马棚牛圈或檐下廊边。老妈妈从记事起就住在一个炒青稞的破棚子里,以后又住在马棚里。她8岁开始接替母亲干活,先是给谿卡堆老婆带孩子,大点了,就煮“羌”,拈毛线,放牛、铡草。每天早上,聂巴发给一点糌粑,一碗清茶,一点点酥油,劳动一天,晚上喝一顿糌粑糊糊。就这样给谿卡当牛马,整整干了60年。冬天,风雪吹进破棚子,她在破毛褐子衫下缩蜷着,象睡在雪窝里。夏天雨水流进了马棚,夜里醒来,全身泡在和着马粪尿的雨水里,没有干地方可以躺一躺。放牛出去,一天不能回来,如果天下雨早回来,就遭聂巴恶骂毒打。老妈妈一生没有丈夫,她和一个在谿卡支乌拉的人要好,生了两个孩子。第一个是男孩,生下就饿死了。第二个女儿活了下来。生孩子也在马棚一角,身子虚弱,好心的其他朗生帮她向主人要了点糌粑。
老妈妈40多岁时,有一次铡草铡掉了一个手指,鲜血象壶嘴倒水样向外流,她昏过去了。15岁的女儿珠玛哭喊着:“妈妈手指铡掉了!”边哭边报告谿卡堆、聂巴,但没人理她。老妈妈醒来时,只记得有条狗把她的手指叼跑了。没有药,也没东西包扎,眼看着手指向上烂。后来还是一个朗生想了个办法。他弄来了些酥油,煎得滚开,把老妈妈的手指残根放在滚开的油里,老阿妈又一次疼得昏了过去。这样,手才没有烂掉。她死活主人不管,可是铡掉了手指第二天,聂巴就派她放牛去了。66年了,她没住过房子,没穿过鞋袜,没吃过饱饭,没穿过一件完整的衣服,也没有自己的家,这就是一个朗生典型的一生!
老妈妈的外孙女,因为食物不足,瘦小得很,4岁了还不会说话。我们问孩子的爸爸是什么人,老妈妈望着一棵大树说:“不知道谁是她爸爸,可怜的孩子,就象这树上的叶子一样啊!”
版权声明:凡注明“来源:中国西藏网”或“中国西藏网文”的所有作品,版权归高原(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任何媒体转载、摘编、引用,须注明来源中国西藏网和署著作者名,否则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中国西藏网微博
中国西藏网微博 中国西藏网微信
中国西藏网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