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初的切蹉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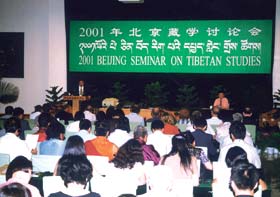 |
| 7月25-29日,北京藏学讨论会召开,图为25日上午大会发言会场。 |
25日上午,讨论会正式召开,这也是本次会议唯一的一次大会,没有开幕仪式,没有领导出席或讲话,藏研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简短致辞后,立刻进入大会发言。像上届一样,会议仍采取无主题讨论会的形式,每位发言15分钟后,听众就此提问、交流。
下午,学者们分为8个学科组,对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社会发展、经济建设、历史、宗教、文学、语言文字、藏医药学等学术领域进行成果交流和学术研讨。
“我们无法接受六世达赖成为外国人”
1911-1949年国民政府对西藏的施政,历来是国内外藏学界十分关注的话题。25日上午,来自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冯明珠研究员,选取1943-1947年英印侵入康藏境域事例,对国民政府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采取的因应措施,进行了专门的探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印度本土的反殖民独立运动日趋激烈,英属印度政府惊觉到,英国势力即将自南亚地区撤退,中国势必利用战胜国的优势恢复对西藏的治权,为了确保英国经略西藏的成果,最好在英国势力撤离前,促成西藏“独立”,并由英属印度政府与西藏直接议定印方称之为“东北边境特区”(The 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的疆界。1943年春天,英属印度政府派遣一支约40余人的劲旅(另有40名背夫),在英国驻阿萨姆(Assam)之萨地亚(Sadiya)长官带领下,进入西康省察隅(Zayul)之瓦隆(Walong)地方,在这里开路修桥、修建营房,辟建机场,准备久驻占领;并深入科麦县昂曲宗(Ko-mei, Sanga)竖立界碑;并向当地西藏驻官要求划定藏印边界。由此在国民政府、英属印度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了一连串的交涉。如1944年锡金政治专员古德(Basil Gould, the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使藏,1945年9月新上任的锡金政治专员霍普金森(J.E.Hopkinson)抵达拉萨,都提出议定这段中印边界的要求。
 |
| 冯明珠研究员关于“国民政府对英印入侵康藏事之因应”论文十分抢手。 |
关于这段中印交涉经过,许多论述近代西藏发展史的著作都曾提及,其中较为详细的有兰姆《西藏、中国与印度》(Tibet, China and India, 1914-1950),梅戈尔斯坦(Melvyn Goldstein)的《喇嘛王国的覆灭》(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周伟洲著《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编《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及李安世《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等,遗憾的是这些著述都只关注于英属印度政府与西藏的交涉,忽略了当时作为西藏主权国的国民政府所扮演的积极角色;有些书中如兰姆及周伟洲的论著虽有提及,但仅及于驻藏办事处代表沈宗濂与印方的交涉。
依据现存台北国史馆的国民政府外交档案,包括“英印侵略西康边境案(一)(二)”、“关于藏案会议案(1944年5月26日至34年9月7日)”、“英对藏宣传独立案(1944年8月8日至36年12月18日)”“废除中英关于西藏之不平等条约案”及现藏台北蒙藏委员会的“驻藏办事处档”等原始档案,冯明珠研究员指出,事实上,国民政府对于英属印度的侵藏行为是非常注意的,并展开了一连串的行动,如动员西康、云南两省力量深入察隅等处实地调查,交通部根据修筑中印公路的经验,对英印在此开路、辟建机场的行动与目的进行评估,蒙藏委员会则密切注意拉萨动向与态度,随时向中央提出报告;外交部则主控全案,汇集各方面报告,爬梳真相,直接向国民政府最高决策机构军事委员会报告,秉承决策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与交涉,并将交涉结果透过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转告藏方等。不过,由于种种缘故,国民政府在处理此次事件中显得消极缓慢,从1943年春英印入侵,到外交部向英国提出口头质疑(1945年1月16日)竟长达两年之久,正式提出交涉则更是在三年半以后(1946年7月2日)。
冯女士的话音未落,会场上已高举起一条条手臂。有的人增补史料,有的指斥国民政府交涉不力,有的指斥英印侵略,最有代表性的是原藏研中心总干事多吉才旦先生,他说,“印度先后占领我9万多平方公里土地,这些印占区一旦真正成为印度地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就成了外国人,这在我们来说,从感情上就接受不了;我们才华横溢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就成为了外国人,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这些地区印度必须归还我们。”老人的悲愤之情、凛然之气,溢于言表,获得满堂学者的认同。
藏区天然林保护与森林的可持续经营
 |
| 吴景山研究员展示他在安多藏区发现的金石碑铭,引得学者纷纷离座观摩。 |
青藏高原上的原始森林占全国总面积的9.59%,主要分布在包括川西北的甘孜、阿坝、甘肃甘南、青海的东部以及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和西藏东南部的林芝和昌都等藏族聚居区。1998年,中国政府启动“西部大开发”工程时,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作为其根本,开始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即首先从青藏高原的东南部、长江、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天然林一律全面禁止采伐,实施封山管护,关闭木材交易市场等。但是,这个工程的启动,却使林区各级政府和人民过去来自森工企业或林副产品的收入大幅度下降,对当地居民建房、燃料等日常生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实现天然林保护和藏区社会经济发展双赢?
藏研中心研究员格勒提交的《关于藏区天然林保护与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几个问题》,以他2000年对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奔孜拦乡和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木尼沟乡两个地区的实地考察,提出:1、在广大藏区,佛教僧人和寺院是保护野生动植物和自然环境的最活跃、最积极的成员,因此在藏区实施天然林禁伐项目,应吸收寺院和僧人的参与;2、1998年前,采伐木材出售和运输成为这些地区藏族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实施天然林停伐政策必须考虑到他们的损失,作出相应的补偿,使其生活不断改善;3、天然林保护工程,使工程区内的农牧民面临燃料、照明、取暖、建筑材料等四难,应开发利用替代木材的新燃料,如太阳能、沼气、风能、小水电站等,逐步减少居民对木材的依赖性;4、藏族林区文盲率普遍较高,云南德钦竟高达59.35%,应在林区投资一些有利于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教育项目,让更多的藏族青年从依赖和破坏森林的传统致富产业走向使森林可持续经营的产业上来;5、一定程度上,家庭仍是项目区的主要社会和生产单位,因此区内投资应向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活动倾斜,包括发展家庭民族手工业、纺织业、承包育林业、旅游业等;6、培训当地藏族农牧民种植、加工、销售一些具有较好市场的新经济林品种,以吸收剩余劳动力,增加农牧民实际收入;7、近几年国家对藏区“天保”工程和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及森林可持续经营等项目投资力度不断加大,严格管理和监督各地项目基金的拨付、使用是项目成功的关键之一;8、从长远看,要保护好天然林,最终必须促进林区农业劳动力从单一的农业或种植业向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转移,这是退耕还林、保护生态、脱贫致富、改善生活的必由之路,也是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的客观要求。
格勒博士的报告就像在一锅油里撒下一把盐,天然林保护、生态环境,学者们都有满肚子的话说。美国新一代基金会(Future Generations)副主席苏君玮女士说,80年代,她第一次进藏,下了飞机后乘吉普车前往林芝,一路上数见28辆满载圆木的大卡车出来,以为林芝的森林一定全毁了,没想到不到工布江达,就见满山满坡的树,直冲云霄;越往里走,树干越粗,都是原始森林!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尽管这样,她并不以为人们可以任意采伐。因为这些原始森林是西藏林芝的,也是世界的,特别是处在青藏高原这样一个世界屋脊上,更应该加以保护。因此,从那时起,新一代基金会就在西藏支持其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和建设,并取得相当的成就。
藏族信仰、民俗文化的变迁
 |
| 苏姗女士报告《哥伦比亚大学藏学研究的发展》。 |
广大藏族人民长期生活在浓郁的藏传佛教文化氛围中,形成独特的信仰文化,近几十年来,随着藏族社会的巨大变革和进步,这种信仰文化也在不断变化。蒲文成先生在《藏族信仰文化的历史变迁与社会进步》中,具体分析了这些变化:1、信仰观念趋于淡化,宗教观念不再占主导地位,人生着眼点开始转向对现世幸福的追求;2、传统“政教合一”制度被废止,藏传佛教的政治作用因失去官方支持而削弱,只在民族经济、文化的纽带联系及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方面发挥作用;3、寺庙数量减少、规模趋小、僧尼人数下降,使信仰的表现程度趋于弱化;4、寺院经济结构方面失去行使剥削手段的生产资料占有,各寺院普遍开展多种形式的“以寺养寺”活动,补充了当地的主流经济,减轻了群众的负担,也利于宗教职员观念的转变,树立“人间佛教”思想;5、信仰方式、规模等外化形式日益贴近世俗社会,非正统的民间信仰更具世俗功利性,规模趋小,内容简化,并增加新的内容,利于与社会相适应;6、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加强,藏族传统文化得到国家的重视和保护,国内外藏学研究日益开展和深入,藏传佛教信仰文化日趋开放,走向世界。
西北民族学院藏族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助理研究员岗·坚赞才让则注目于藏族民俗的变迁,认为随着商品经济意识和现代化大生产带来的竞争意识,使扎根千百年的各种传统观念和习俗逐步改进,从藏族的衣食住行等民俗文化的表象层次上的时代特色,就能看出民族传统的社会模式发生变化。1、行为,传统文化中的重义轻利、鄙视商人、耻于经商、不愿参与竞争等观念逐步改变,表现在原以宗教和娱乐为主旨的节日活动,物资交流活动成了主要内容,一些传统节日文化已集文化、商贸和娱乐于一身;2、居住,帐篷、房屋等传统主体样式和风格依然保留,但人们根据实际需要,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风格,在设计、装修等方面发生大的变化,有条件的还用进口材料装修,讲究坚固、舒适和方便;3、服饰,由于自然环境,藏袍、皮袄仍是藏民族主体服装,但穿西服、休闲服、时装、牛仔服等各式服装的也大有人在。这种变化在民族杂居区、农业区比较明显,而在与外界来往比较困难的牧区也随处可见;4、饮食,传统的酥油茶、糌粑、手抓羊肉、青稞酒等仍然深受藏族喜爱,但人们也开始讲究饮食营养、卫生,不管夏天还是冬天,农牧区的大街小乡都能看到摆摊卖菜卖水果的;以往禁吃的鱼已成为餐桌上的佳肴,而藏区的特产牛肉干、奶粉等也销往国内外。这些日常生活习俗上的变化,表明藏区正在走向现代化。
几点倡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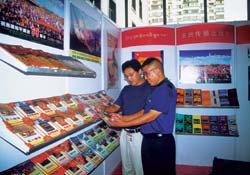 |
| 藏学图书展览上的精美图书。 |
1985年出版的《藏汉大辞典》,其水平超过以前所有一切的藏文词书,国内外对此评价甚高。但该书出版后不久,编纂者很快发现其中的一些错误,向责任编辑提出,1986年第二次印刷时作了约100条的修正。由于当时印刷条件限制,只能在不动原版面的情况下进行挖改填补,不能作太大改动,更不能增加。事过十多年,各方面条件都有了变化,对《藏汉大辞典》的增订再版的时候到了。对此,中国国家图书馆资深研究馆员黄明信先生刍议发动广大的藏文书籍读者、藏学工作者和专家集思广益,共同完成,并提出许多具体建议,得到大家的高度肯定,王尧、黄颢等教授提议将此项建议列为单项,上报有关部门。陈庆英研究员还进一步提出要在新出《藏文大藏经》的基础上,对大藏经中的词语加以整理出版,编纂一部藏文藏汉对照大藏经大辞典。
会议期间,中国藏学出版社、民族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外文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以及青海、甘肃、四川等省的民族出版社等9家联合举办了藏学书籍展销,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兴趣,特别是来自港台地区和国外的学者们,大多是满载而归。不仅如此,他们还提议建立藏学图书信息、销售中心,以使广大的研究者能更直接、方便地共享研究资料,而不仅仅是只有到中国参加藏学会议才能买到图书。
会议期间,学者们参加了藏研中心北京藏医院举办的藏药展销和两次藏医药学讲座,参观了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文物珍品特展,青海黄南州举办的热贡唐卡艺术展览,魏克先生珍藏的西藏邮史展览。会后,17位海外学者还前往西藏自治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学术考察。
版权声明:凡注明“来源:中国西藏网”或“中国西藏网文”的所有作品,版权归高原(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任何媒体转载、摘编、引用,须注明来源中国西藏网和署著作者名,否则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中国西藏网微博
中国西藏网微博 中国西藏网微信
中国西藏网微信






